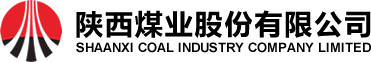我至今还记得张老师的第一堂课。
那年我十三岁,刚上初中。教室里弥漫着新书本的墨香和乡下孩子身上特有的泥土气息。上课铃响过三遍,教室里仍嗡嗡作响,像一窝被捅了的蜂巢。
门轻轻开了,她走进来,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衫,两条乌黑的辫子垂在胸前,手里捧着一摞作业本。最引人注目的是她那双眼大而明亮,像山涧的清泉,却又藏着几分怯生生的神色。
“同学们好,我是你们的语文老师,姓张。”她的声音轻柔,却意外地穿透了整个教室的嘈杂。调皮的王小虎在下面学了一声猫叫,引得哄堂大笑。张老师的脸霎时红了,那双明亮的眼睛里似乎有什么东西闪了一下,却又迅速消失。她什么也没说,只是轻轻翻开课本:“今天我们学习朱自清的《背影》。”当她读到父亲爬过月台为儿子买橘子的那段时,声音微微发颤,我抬头望去,惊讶地发现她的眼角闪着泪光。教室里安静极了,连最顽皮的学生也屏住了呼吸,那是我第一次看见老师在课堂上动情。后来才知道,张老师是从省城来的大学生,自愿到我们这穷乡僻壤的地方支教。
有一次,我去办公室交作业,无意听见老校长对她说:“小张老师,真是委屈你了,这些乡下孩子野惯了,不好教。”张老师笑了:“校长,孩子们都很聪明,只是需要有人引导。”
期中考试后,我的作文破天荒得了全班最高分,张老师让我课后去她办公室。我忐忑不安地推开门,看见她正伏案批改作业,夕阳透过窗棂,为她周身镀上一层金边。“你的作文写得很好,”她指着本子上红笔批注的密密麻麻的字迹,“特别是描写你母亲深夜缝补衣裳那段,很真实,很动人。”
我低着头,心跳得厉害。“你有写作的天赋,”她继续说,声音里透着真诚的喜悦,“坚持下去,将来也许能成为作家。”那一刻,我心里感受到有什么东西被点燃了,从来没有人对我说过这样的话,更不用说是一位从省城来的老师。
然而好景不长,一个飘着细雨的午后,教室里异常躁动。课前,王小虎不知从哪听说张老师要走了,消息像野火般蔓延开来。张老师走进教室时,明显感觉到了异样,她试图开始讲课,但台下窃窃私语不断。“老师,您真的要走了吗?”终于,一个胆大的同学问道。张老师愣住了,手中的粉笔“啪”地断成两截。她沉默良久,才轻声说:“是的,月底就要走了。”教室里顿时炸开了锅,有同学开始哭泣,更多的人则七嘴八舌地问为什么。“安静!”张老师提高了声音,这是她第一次对我们这么大声说话。教室里立刻静了下来。她看着我们,嘴唇微微颤抖:“因为我母亲病重,需要人照顾,我……我也舍不得大家。”突然,王小虎站了起来:“您骗人!我听校长说,是因为咱们学校太穷,请不起省城的老师!”
张老师的脸一下子变得苍白,她张了张嘴,似乎想说什么,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。那一刻,我看见泪水在她眼眶中聚集,越聚越多,终于夺眶而出,顺着脸颊滑落。那不是一滴滴的泪,而是连成线的溪流,无声地流淌着,她没有擦拭,任由它们肆意奔流。
教室里寂静无声,只有窗外的雨淅淅沥沥下着,突然,王小虎“哇”地一声哭了出来:“老师,对不起!我们不想您走!我们以后一定好好学习!”此时此刻,仿佛打开了某种闸门,教室里顿时哭声一片,几十个乡下孩子,用最质朴的方式表达着心中的不舍。张老师终于抬手擦了擦眼泪,努力挤出微笑:“别哭,都别哭,无论我在哪里,都会记得你们的,你们要答应我,好好学习,将来走出农村,去看更广阔的世界。”那是我人生中最漫长的一堂课,没有课本,没有板书,只有眼泪和承诺。
月底,张老师真的走了,临走前,她给每个同学都送了书,给我的是一本《鲁迅小说集》,封面上写着:“保持你对生活的敏感和真诚,它会让你写出动人的文字。”
当我再次见到老校长的时候他已经退休,他告诉我一个秘密,当年张老师并非因母亲病重离开,而是被教育局调走的,有人举报她“教唆学生思想偏离正轨”,只因她鼓励我们阅读课外书,思考外面的大千世界。“她走的那天,哭成了泪人,”老校长说,“她最放不下的就是你们这些孩子。”恍惚间,我脑海里出现了那间熟悉的教室……阳光透过窗户,尘埃在光柱中飞舞,那个穿着蓝布衫的年轻老师,看见她眼角那滴始终没有坠落的泪。
我常常在想,有些眼泪,不为自己而流,却滋润了另一片生命的原野,而张老师的眼泪,落在我们心上,发芽,开花,结果。多年后,我虽未成为作家,但从事的是思想政治工作,而今我算是企业“播种”的人。教师节来临,那一滴泪的重量,足以让我再次想起那个对我影响颇深的良师。(马晴盼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