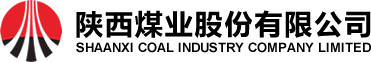我的女儿生在岭南,祖籍在鄱阳湖畔,从血脉上讲是个地道的南方姑娘。可我却暗自庆幸,她是长在北方的南方姑娘。
那道横亘在中国版图上的秦岭—淮河线,不仅划分了南北地理,更划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农耕文明。南方的水田里生长着温婉的稻米,北方的旱地上挺立着坚韧的麦穗。一方水土养一方人,这方水土孕育的不仅是作物,更是一种深入骨髓的生活方式。
北方大地在春意暖阳中苏醒,我牵着女儿的小手走向田野。
“哆哆,看,这就是麦田。”
“妈妈,它们好像韭菜啊!”
女儿天真的话语让我哑然失笑。这个在绘本里认识世界的小姑娘,何曾见过真正的麦苗?那些关于割场、铡麦、轧场的农事记忆,在我们这代人的脑海中已然模糊。农村城市化、农田机械化,传统的劳作场景成了遥远的回忆。
坐在田埂上,三十年前的夏夜忽然浮现在眼前。那时母亲独自去“浇地”(韩城方言,意为灌溉麦田),六岁的我和弟弟放心不下,偷偷跟去做伴。月光下的麦田泛着银光,母亲的身影在田垄间穿梭。
“为啥要半夜浇地?”稚嫩的声音在夜色中格外清脆。
母亲说,村里每年到浇麦子时节,都统一开泵放水,按照责任田的顺序挨家挨户排队漫灌,轮到自家时已是深夜。没有手机的年代,要时刻盯着水流,一亩地浇两个多小时,收费六块钱。她教我们听水声辨流速,看田埂防漫灌。正说着,母亲突然一个箭步冲进夜色,裤腿擦过麦穗的沙沙声渐行渐远。二十分钟后,她喘着气回来:“差点淹了邻家的地。”
母亲不愿我们重复她面朝黄土的命运,却执意要教会我们这些土地赐予的智慧。
芒种时节,南方的水田里秧苗青青,北方的麦地已是一片金黄。小麦与玉米不同,它娇贵而执着,从秋分到芒种,要经历八个节气、二百七十个日夜的守候,才能换来这一季的丰收。
记忆中的麦收时节,大人们挥镰如飞,孩子们跟在后面拾穗。烈日下的西瓜格外清甜,晒场上的麦粒散发着阳光的味道。交公粮的日子,乡亲们把最好的粮食送往粮站(2006年之前要交农业税),余下的才留作口粮。土地多的人家尚可温饱,地少的人家却要节衣缩食。但他们从未迟疑,这是对土地最朴素的忠诚。
前些日子,爱人买来草莓苗,我们为种植方法争执不下。他要去问“AI”,我笑说家里两位“老把式”还用请教机器人?父亲笑着指点,末了叹道:“种了一辈子地,临了却没了田地。”
中国人骨子里对土地的眷恋是藏不住的。住进楼房的老人们把花盆改成菜盆,泡沫箱里种小葱,油桶里栽辣椒。故乡因工业发展搬迁,父母住进了梦寐以求的楼房,眼中的落寞却多过欢喜。母亲说:“有土的地方才能扎下根,心才踏实。”
我让女儿捧起一捧麦穗,感受土地给予辛劳的馈赠。农人的品格就像这麦子,你付出多少汗水,它就回报多少金黄。这份质朴的道理,不仅适用于土地,更是为人之本。
在这快速变迁的时代,那一垄麦黄所承载的,不仅是粮食,更是一个民族最本真的记忆。女儿将来长大,或许她不会记得麦苗与韭菜的区别,但我希望她能记住:生命如麦,需要时间的沉淀,需要耐心的守候,才能迎来属于自己的金黄时节(卫宝娜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