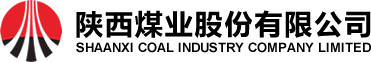七十年代的蒲白白水煤矿矿区街道,煤渣路踩上去沙沙响,两旁的土坯房矮矮地挨在一起。其中一间挂着“刘家羊肉”蓝布幌子的屋子,是矿工们最惦记的地儿——不是职工食堂,是老刘开的私人小馆。几张掉漆的木桌摆得挤挤当当,墙角堆着劈好的柴火,风从门缝钻进来,裹着屋里的羊肉香,老远就能勾住人的脚步。
每天早上七点左右,店里最是热闹。休班的矿工换了干净褂子,揣着皱巴巴的毛票往馆子里钻,手里除了攥着两个自家蒸的馒头,多半还揣着几瓣生蒜——生蒜是陕西人吃羊肉泡的灵魂,哪能离得了?这不是啥讲究,是刻在骨子里的习惯,就像吃面要就醋,少了蒜,连汤的香味都像差了半截。那会儿收入不高,自带馒头能省点钱,兜里揣的这两瓣生蒜,都是配羊肉泡的“硬货”。
矿区人都把刘胜利叫老刘。老刘系着灰布围裙在灶前忙,铁锅里的羊骨炖得咕嘟响,汤熬得稠稠的,舀一勺能看见底儿的鲜。有人凑到灶前喊:“老刘,给多搁块肥的!”不像现在人都爱挑瘦的,那时候肥羊肉才是正经味——本地山羊的肉,肥膘炖得软乎乎,咬一口,油香混着肉香,鲜得能把舌头吞下去。盛汤用的是粗瓷老碗,碗沿磕了好几道豁口,却不妨碍它装得满当当。矿工们接过碗,往桌角一放,先掰一瓣蒜搁嘴里嚼,辛辣劲混着肉香往鼻尖钻,顿时就觉得浑身都活泛了。
大伙找个空位坐下,有的干脆蹲在门口台阶上,把馒头掰成小块往汤里泡。隔壁桌的老张刚咬一口泡馍,就着蒜含糊地跟对面的小李搭话:“昨儿井下三号巷的支架稳当不?我瞅着前儿有点晃。”小李扒拉着碗里的肉,也嚼着蒜应:“放心吧张师傅,当天夜班就加固了。你休班这两天,队里还新换了照明灯呢。”话音刚落,旁边蹲台阶的老王接了茬:“要说还是现在好,搁前些年,井下哪有这条件?就这羊肉泡配蒜,搁三年前,我都舍不得每月吃一回,现在好歹能凑着休班就来解解馋。”
没人细琢磨这话里的苦乐,都只顾着手里的碗——第一碗先泡半个馍,就着蒜呼噜呼噜吃完,汤见了底,就端着碗喊老刘:“再续点汤!” 碗底留着的几块肉,混着新续的热汤,再泡剩下的馒头;蒜瓣嚼完了,就再摸出一瓣,慢慢嚼,细细咥。聊几句井下的活计,说两句家里的琐事,一碗汤泡两个馍、几瓣蒜的功夫,浑身的乏劲就跟着热汤散了。
如今再走矿区街道,当年的土坯房早换成了砖瓦房,“刘家羊肉”也翻了新——亮堂的玻璃窗,干净的木桌,一份二十多块钱,配着现烤的烧饼,桌上还摆着剥好的糖蒜、腌蒜,精致得很。矿工家属们坐下就说“要瘦的”,烧饼掰得匀匀的,泡在清亮的汤里,也会就着蒜吃,却少了当年蹲在台阶上、从兜里摸出瓣生蒜就着热汤嚼的粗粝热乎气。不是现在的羊肉泡不香、蒜不对味,是那年月里,揣着馒头和生蒜凑在一块儿咥饭的日子,藏着矿工们最踏实的烟火气,是再也回不去的、属于老矿区的旧时光。(赵洁洁)